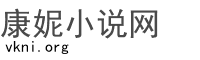孙皓晖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康妮小说网https://www.vkni.org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谁也没想到,皇帝即位后首次朝会,发生了如此突兀的变化。
这是皇帝首次大朝会,轴心议题早已知会了所有官署——确定国家治道。朝会伊始,皇帝刚刚申明了主旨,丞相王绾第一个出班奏对。依照新朝仪,王绾站在自己的座案前,捧着上书高声念诵:“臣,丞相王绾,昧死有奏皇帝陛下,主张新朝奉行诸侯制。臣呈上奏章——”于是,众目睽睽之下,殿前御史接过了新朝第一道奏章,双手捧到了始皇帝案头。大殿群臣始而惊讶——历来只处置政务而不提政见的老丞相竟能发端大政,继而恍然——新朝遵奉何等治道,非老丞相发端莫属。于是,一时纷纷议论。
正当此时,博士仆射周青臣霍然站起,高举上书高声念诵:“臣,博士仆射周青臣,昧死有奏皇帝陛下,呈上博士七十人联具之《请行封建书》——”殿东一大片博士整齐站起,齐声高诵:“臣等昧死启奏皇帝陛下,请行封建,以固大秦!”如此声势,又一齐口称“昧死”,秦国庙堂见所未见。一时群臣彷徨,有诸多元老便要站起来呼应。
目下王绾与众博士口称昧死,可谓既表惶恐,又表忠心,亦表无所畏惧。就其本意,无疑与“斗胆直言”之类的表白相近,本无他意。然在质朴厚重的秦国朝会上,大臣言事历来极少这种自我表白,有事说事罢了。如今老丞相慷慨发端,一大片博士慷慨相随,人人昂昂高呼“昧死以奏”,大臣们如何不怦然心动?
“臣,通武侯王贲有奏。”
一声浑厚而沉稳的宣示,大殿中立刻肃静下来。谁都知道,王翦、王贲父子连灭五国,在新朝具有无与伦比的分量。更有一点,父子两人都是寡言之人,朝会极少开口,开口则绝不中途退缩。当此之时,王贲挺身而出,定然大事无疑。举殿肃然之间,王贲前出两步,捧着一卷竹简高声道:“臣与关内侯尉缭联具奏对,请行郡县制,今呈上奏章。”殿前御史接过竹简,王贲坐回了班次。如此两位重臣与丞相大相径庭,主张郡县制,群臣顿时清醒,不再急于附议,一时方安静了下来。
“老臣有奏……”王绾再度慷慨奏对。
“朕有决断。”皇帝开口了,打断了王绾。
嬴政第一次使用这个拗口的自称,有些生硬,也渗出几分冷冰冰气息,“丞相、博士学宫、通武侯、关内侯,各有奏章,且主张已明。当下议决,未免仓促。朕之决断:发下今日三则奏章,各官署集本部官吏议之,或酿成共识,或两分亦可;旬日之后,朝会一体决之。散朝。”说罢,皇帝径自走了,朝会散了。
咸阳各官署,及所有新设郡县官署,都开始了轰轰然议政。
嬴政深感朝会出乎意料,散朝后立即召进李斯、王贲会商。
李斯说:“博士学宫联具请行封建,意料之中不足为奇;大秦开创新制,若没有诸侯制声音,反倒是怪事了;老丞相王绾不事先知会,突兀力主诸侯制,才是真正的棘手。”王贲说:“老丞相历来与闻决策,该当明白君上等图治趋向,今突兀转向诸侯制,完全可能引发大局动荡生变。”李斯深表赞同,补充说:“此等动荡与其说迟滞郡县制推行,毋宁说为天下复辟者反对郡县制,立下了一个新的根基,后患多多。”蒙毅则以为:王绾突兀发难,很可能是受了博士们煽惑,未必自家真心主张;其中根源,必是王绾自觉新政轴心不在丞相府所致。
“不。三处须得澄清。”一直凝神倾听的嬴政轻轻叩着书案,“其一,王绾之举,绝非突兀。其二,王绾主张,绝非复辟。其三,王绾之心,绝非自觉权力失落。不明乎此,不能妥善处置纷争。”
“君上三说,依据何在,敢请明示。”王贲一如既往地直率。
“先说一。”嬴政顺手从文卷如山的旁案拖过一只早已打开的长大铜匣,拿出一卷竹简展开在案头,“这是《吕氏春秋》,两位可能不熟,廷尉该当明白。《吕氏春秋》明白主张封建制,且是众封建,诸侯封得越多越好。王绾素来信奉吕学,未尝着意隐瞒。当此之时,王绾必感事关重大,而又无法说服我等君臣,故联手博士,形成朝议对峙,逼交公议而决。显然,老丞相是有备而来。三位皆曰突兀,在于忽视了王绾治学根基,似觉老丞相没有理由如此主张。可是如此?”
“君上明察!”三人异口同声,李斯犹有愧色。
“再说二。”嬴政指点着案头书卷,“王绾主张封建诸侯,基于治国学说,基于安秦另一思路,而非基于复辟远古旧制,更非基于复辟六国旧制。此与当年文信侯根基同一。六国王族、世族鼓荡封建诸侯,则是明白复辟。即或博士学宫七十博士主张封建诸侯,一大半也是基于治学信奉不同,也非世族复辟之论。”
“君上明察!”
“再说三。”嬴政又从旁案拖过一只木匣,拿出一卷道,“灭楚之前,老丞相曾经上书请辞,理由是‘治事无长策,步履迟滞’。十余年来,老丞相勉力支撑,未尝一事掣肘,纵无大刀阔斧,亦绝非纠缠权力进退之辈。”
“臣之指斥,草率过甚。”蒙毅当即肃然长跪,拱手如对王绾致歉。
“凡此者三,决我方略。”嬴政继续道,“一则,唯其王绾有吕学根基,有备而发,两制之争当认真论争,绝不草率从事。二则,唯其老丞相博士等非六国王族世族复辟之论,两制之争当以政见歧异待之;纵有后患,届时再论。三则,唯其老丞相非关私欲,两制之争不涉国政权力。”
“臣等赞同!”
“君上方略至当。”李斯一拱手,心悦诚服愧色犹在,“王绾之于吕学,臣疏忽若此,深为惭愧也。今据君上处置两争方略,臣以为根本在第二则,即以政见歧异待之。既为政见之争,必涉吕学与诸家之道。此,臣之所长也。臣自请主力,与老丞相等一争是非曲直。”
“廷尉主力,正当其时!”王贲拍掌大笑。
“《吕氏春秋》乃廷尉当年总纂,正当其人。”蒙毅也和了一句。
“廷尉主战。”嬴政一拍案,“然此事至大,不能廷尉孤军独战。”
“陛下毋忧,我等当妥为谋划。”不期用了新称谓,李斯自己也笑了。
“臣等与廷尉协力!”王贲、蒙毅立即跟上。
“好!两制之争乃华夏根本,务求全胜。”
“赳赳老秦,共赴国难!”
李斯、王贲、蒙毅不期然异口同声冒出一句久违了的老秦誓言,一时君臣四人的眼睛都潮湿了。
在嬴政君臣筹划之时,各署议治的消息也纷纷激荡开来。蒙毅总司中枢,络绎不绝的消息都是“本署多以封建诸侯为是,以郡县制为非”。蒙毅非但备细阅读了每一份呈报进皇城的议治书,还亲自赶赴丞相府、上将军府、大田令府、司空府、司寇府、内史府、博士学宫七大最主要官邸分别听了议治论争,终于对种种纷争大体清楚了。
始皇帝元年六月初,一场创制大论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除了王翦、蒙恬与戍守陇西的李信,所有在外大臣与已经有稳定官署的郡守县令,都被召回了咸阳。更有不同者,大殿内皇帝阶下专设了皇子区域,二十余名皇子全部与朝。咸阳所有官署的所有官员,除了有秩吏之下的吏员,举凡官员一律与会。素常宽阔敞亮的正殿,黑沉沉一片六百余人,第一次显得有些狭小起来。卯时钟鼓大起,帝辇在迭次长呼中徐徐推出。高冠带剑的皇帝稳步登上帝座,大朝会宣告开始了。
“诸位,朕即皇帝位,今日首议大政。”
所有殿门与所有窗户全部大开,沉沉大殿在盛夏的清晨颇见凉爽。皇帝一身冠带,平静威严地继续着主旨宣示:“天下一统,我朝新开。行封建诸侯,或行郡县一治,事关千秋大计。日前,首议三奏业已发下,各署公议也大体清晰。归总论之,主张依然两分。今日大朝,最终议决,朕将亲为决断。朝会议政,不避歧见,诸位但言无妨。”
“臣博士鲍白令之敢问,陛下对新制大计定见如何?”
“大朝议政,不当揣摩上意。”皇帝冷冰冰一句回绝了试探。
“臣,博士仆射有奏。”西边文职大臣区后的博士区,昂然站起了掌持博士学宫的周青臣,慷慨激昂道,“皇帝陛下扫灭六国,威加海内,德兼三皇,功过五帝,为千古第一大皇帝也!然则,平海内易,安海内难。天下九州,情势风习各异,难为一统之治。大秦欲安,必得以《吕氏春秋》为大道,众封建。封诸多皇子各为诸侯,辅以良臣,因时因地而推治,如此天下可定也!”
“臣,博士淳于越附议!今皇帝君临天下,四海归一,当继三代之绝世,兴湮灭之封国,使诸位皇子、开国功臣,皆有封国之土,皆有勤王之力!如此封藩建卫,土皆有主,民皆有君,皇帝陛下亦省却治民之劳,郁郁乎文哉!泱泱乎大哉!”这位素有稷下名士声望的淳于越跟了上来,文臣坐席区诸多要员顿时振作瞩目。
“臣,博士叔孙通转呈山东游士奏章!”
一言落点,举殿惊讶。朝会者,君臣之议也,是为朝议。游学士子为庶民,为野议,为民议。野议民议,无固定程式,也并不包括在君主“下议”的议事制度内。然则,中国族群自远古以来,即有浓厚的野议之风,也有许多相应的上达形式。战国之世,重视野议之风犹在。庶民野议但以上书方式呈现,往往是最为重大的民议,甚或被视为某种天意。当此重大朝会,陡然出现野议奏章,此间意蕴难以逆料,大殿群臣立即静如幽谷。
“既有野议奏章,当殿宣读可也。”皇帝说话了。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