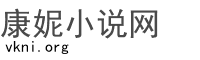小说故事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康妮小说网https://www.vkni.org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第6章 仇国论
李平万万料不到,丞相回到汉中,并不打算再图北伐,也不回南郑家中休养,而是安顿大军之后,与杨仪、关兴前往成都见驾。
此时张苞染病,孔明也令人把他送往阆中老家养病。
孔明去后,李平又提心吊胆起来。
孔明此行,是因心中疑团未解,却又不便追查,这才匆匆前往成都。
他认为狐忠、成藩就是有包天之胆,也不敢假旨叫他退兵。他们说得清楚,是奉李平之令,前来谕旨,而李平又先声夺人,反问粮草充足,为何退兵?
这里面到底是李平假旨?或是后主确有退兵之意,又不敢做主,这才造成事实之后,把责任推到狐忠、成藩身上?
此次北伐,除了天时不利之外,粮草千里转运,确实十分困难。但如果后方供应不断,大军转战陇中,还是可以战胜司马懿。
是什么原因生出退兵的旨意呢?是后主畏敌,是李平转运不力,或是国中实在空虚,完全支持不了北伐的消耗?他想摸清底细,是战是守,再作定夺。
已经五出祁山,连战四年,北伐尚无大的进展,这实在令他痛心。此次若不查明退兵原因,今后再言一统大业,就不知要费多少口
舌了。
后主刘禅得知丞相返都,急忙与侍中郭攸之、董允、费祎和留府长史蒋琬、张裔迎出虎威门。
后主听李平奏报,只知丞相退兵,乃是诱敌之计。想不到丞相停兵不战,返回成都。他一向不过问丞相用兵,也不想知道何故不战。见了相父,只是连连慰说辛苦,到了成都好生安歇之类的客气话,半句不说此次用兵之事。
到了承明殿,后主又赶紧下旨赐座,孔明坚辞不坐,反而跪地奏道:
“圣上可知,老臣这次为何退兵吗?&34;
”相父退兵,不是诱兵之计吗?“刘禅眼睛--眨反问道。孔明---怔,便知狐忠、成潘喻旨退兵有诈,后主根本就不曾下过退兵的旨意,那么是谁假旨呢?
刘禅见问,以为相父又要教训什么,急忙令内侍取出李平的奏章,送到相父手中。
孔明看了李平的奏章,再看落款之日是在他退兵之前。他的大军还没动,李平就知道他要退兵,且是诱兵之计,可见假旨的事与他有关。这个李平真是昏了头了,竟敢假旨骗他退兵。
刘禅见相父看了李平的表章,脸色突变,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,赶紧表白道:
”相父出兵以后,朕就盼着相父早点还都,现在相父回来了,不论是诱兵之计也好,班师回朝也好,朕都很喜欢。“
这话就更加证实,后主并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退兵。狐忠、成藩假旨之后,躲了起来,显然是李平指使。李平假旨破坏北伐,实不可忍。当即,他就请后主下旨,召李平还都。
李平在汉中接旨,就知事已败露。但他不逃,立即动身进都,也不上表向后主禀明原委,竟直接到相府求见孔明。
孔明也不客气,当面出示他给后主的奏章,指出其中破绽。李平无话,坦然承认是他假旨。但诉说他是迫不得已,并将征粮之难,转运之难,以及造成大军断粮将致全军覆灭之忧等等满腹苦水,尽数倒出。
孔明听了大声斥责道:
”你只知你自身之难,却不知国家之难。当初你未北上,镇守江州,曾划五郡,立巴州,任刺史,允你所求。此次令汝督汉中,营粮草,就表封李丰督江州,朝廷可谓有求必应,隆崇其遇。你不思忠报,横造无端,危耻不辨,导人为奸,害得八万大军前功尽弃。罪责如此深重,你还有话辩解?&34;
李平听罢,含羞告退。
次日朝议,侍中郭攸之、董允、费祎,相府长史蒋琬、张裔、杨仪都道李平罪不可赦,当斩。
谏议大夫杜琼,尚书李微、杨洪,祭酒孟光、来敏也都附议当处极刑。
博士尹默、李撰,秘书却正、费诗都是刘璋旧部,又是李严故友,也都不敢保奏,只是低头不语。只有太史谯周出班奏道:
“李平假旨,罪不可赦。但是转运确实艰难,如果他不假旨退兵,军中粮断援绝,又将会是什么结果呢?&34;
谯周言外之意,李严有罪,但还是做了好事,救了丞相的八万大军。
随军长史杨仪听了,不由大怒。他说:
”八万大军冒雨转战,随时都有被歼灭的危险,尚且不畏艰难,浴血奋战。他李平二万人马转运粮草,兵强马壮,还有木牛之利,还敢强调艰难,妄说误事有理,难道他假旨无罪,反而有功吗?&34;
谯周还想争辩,但见各位侍中、长史都是众口一辞,纷纷奏请严惩李平,自知人微言轻,再说情由也救不了李平。但他认为他不仅仅是为李平开罪,他是想让丞相听了,有个反省。
历次北伐,几乎都是空劳师众,无功而返。丞相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总是找一二个人来替罪。第一次失败,归结于“马谡失街亭”,这次失败又归咎于“李平假旨”,却不知根本原因是他的大战略失误。从根本上说,北伐没有意义,光复也没有成功的希望。
“陇中连战三月,汉中粮尽,蜀中粮乏,且不说转运之难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!”谯周忽然转头对孔明这样说道。
孔明听了这话,就知谯周不光是为李平开脱罪责,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他的北伐大略。但他不想当众和这位敢说真心话的太史争辩,眼前应该考虑的是,如何处理李平?既要使他本人心服口服,又要使那些刘璋旧人不会产生误会,认为是他借故排斥异已,打击刘璋旧部。
刘禅坐在那里,只等孔明说话,他并不在乎李平该不该死,他只怕相父叫他作主,使他不知是听众人的好呢?还是听谯周的好?
他只盼这事快一点结束。今天又是吴太后的生日,又会有许多贵妇入宫朝贺,他与其中的一个人,有许多日子没有见面,心里正想得慌。这一次一定要和她多说几句话,多待一会儿,和这种绝色佳人在一起说话,比喝一壶美酒还要醉人。
刘禅正想得入迷,忽听丞相奏道:
“李平假旨,罪不可赦,但也正如谯周所言,确是迫于无奈,请皇上从轻发落。”
“相父你说是杀还是不杀呢?”刘禅没听出孔明的意思,就瞪大眼睛反问。
孔明听了一怔,心里暗恼,这个阿斗,连坐朝都心不在焉。却又不能当众教训,只好一本正经再奏道:
“臣以为念李平前功,可免死罪,削职为民,流徙梓潼,让其反省。”
刘禅马上准奏,立叫费祎颂旨,未等众臣礼赞散朝,他自己匆匆先走了。
孔明本来还要申奏,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,调到汉中参与军事,以免他在江州,听人鼓动,做出不利于国家的事来。
他见后主匆匆退朝,也不便再说,只好回去另修表章上奏了。刘禅出了承明殿,就急急赶往吴太后居住的长乐官。他一边走,一边问身边的小黄门喜富,现在是什么时辰?他怕过了午时,前来朝贺太后生日的贵妇,都出宫去了,他好不容易盼来的机会,又错过了。
喜富知道后主心里惦记着什么,就微笑回禀:
“皇上你看,太阳还没升上殿顶,还不到申时呢!&34;
刘禅抬头一望,果然长乐官前,还罩着承明殿长长的影子,时辰还早着呢。此时贵妇们大概还都聚在长乐官拜见太后,不外是送礼、拜寿、叙话、请用御馔等等琐事。刘禅怕人多眼杂,到了那里反而不便与那人说话,就交代喜富说,稍待车骑将军刘琰的夫人胡氏出来,你对她说,请稍留片刻。朕有御玉一块,要送车骑将军,劳她带回府去。
喜富知道这是后主贪人美色,借故亲近,就赶紧到崇礼门张望等候。
刘禅自到一处偏殿,取出身上的一块玉佩,寻思着如何与胡氏说话,既不失天子之仪,又能同她面对面,坐上许久,说许多话。想到胡氏见他,一定满脸飞霞,低头微笑的娇态,他就更加痴痴地想入非非了。
可是左等右等,一直等到日影过午,还是不见喜富把胡氏带了进来。正要出去问个究竟,喜富匆匆进来襄道:
“胡氏被吴太后留在长乐宫,没有出来。”
刘禅得知胡氏还在,也不管礼与不礼,就径直往长乐官寻去。原来吴太后见胡氏貌美性情温顺,十分喜爱,特意将她留在官中同用午膳,此时正对面坐着,一边说笑,一边吃喝呢!
刘禅见状,对吴太后纳头便拜,口称太后寿庆,朕一步来迟请太后恕罪。人跪在太后面前,眼睛却痴痴地盯在胡氏身上。
吴太后急忙起身扶起后主,说皇上国事缠身,她的生日小庆就不必操心了。说着就叫宫女重摆膳食,欲请刘禅同用午膳。
刘禅正苦不得有此良机,就在太后身边坐下。不料胡氏起身禀道,尊卑有序,内外有别,她不敢与皇上同桌而食,就要告退。
刘禅听了一急,竟忘了吴太后就在身边,急趋上前,拉住胡氏的小手求道:
“千万不要走,朕把你吓走了,岂不扰了太后的雅兴,走不得,走不得!&34;
胡氏突然间被后主拉住手腕,脸上立即泛红,羞答低着头,走也不是,坐也不是。
刘禅只觉得那小手腕既绵又滑,握在手里温温地微微发颤。他立刻就像喝醉了酒似的,头晕晕想倒在她的怀里。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