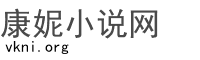孙皓晖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康妮小说网https://www.vkni.org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奇异的事情接二连三,吕不韦实在惊讶莫名。
在他做出部署两日之后的午后时分,主事悬赏的门客舍人匆匆来报,蒙恬在张挂大书的城墙车马场竖立了一座商鞅石像。吕不韦大奇,商君石像如何能矗到车马场去?门客舍人愤愤然比画着,说了一番矗立石像的经过。
“死人压活人,理他何来?”吕不韦冷冷一笑。
于是,舍人又匆匆赶回了南门。一番部署,门客们扎起帐篷轮流当值,依旧前后奔波着,照应围观人众读书改书,鼓呼一字师领取赏金,将庞大石像与守护甲士视若无物。
如此过得三五日,门客舍人又赶回丞相府禀报:车马场被咸阳都尉划作了法圣苑,圈起了三尺石墙,一个百人甲士队守护在围墙之外,只许国人与游学士子在苑外观瞻,不许进入石墙之内。如此一来,民众士子被远远挡在了法圣苑之外,根本不可能到城墙下读书,更不可能改书了。
吕不韦又气又笑:“教他圈!除非用强,《吕氏春秋》不撤!”
出人意料的是,都尉率领的甲士,根本没有理睬聚集在法圣苑围墙内的学宫门客,也没有强令撤除白布大书,更没有驱赶守书门客。两边井水不犯河水,各司其职地板着脸僵持着。门客舍人不耐,与都尉论理,说城墙乃官地,立商君像未尝不可,然圈墙阻挡国人行止,是害民生计。都尉高声大气说,官地用场由官府定,知道吗?圣贤都有宗祠,堂堂法圣苑,不该有道墙吗?本都尉不问你等堵塞车马滋扰行人,你等还来说事,岂有此理!如此僵持了三五日,守法成习的国人士子们渐渐没有了围观兴趣,南门外人群渐渐零落了。门客们冷清清守着白花花一片的《吕氏春秋》,尴尬至极,长吁短叹无可奈何。
“若再僵持,教人失笑。”门客舍人气馁了。
“小子,也是一策。”
终于,吕不韦吩咐撤回了大书。
秋分这日,吕不韦奉召进了王城,参加例行的秋藏朝会。
秋藏者,秋收之后清点汇总大小府库之赋税收入也。丞相领政,自然不能缺席。吕不韦清晨进入王城,下得辎车,见大臣们驻足车马场外的大池边,时而仰头打量时而纷纭低语。有意无意一抬头,吕不韦看见大池中铜铸指南车上的高大铜人遥指南天,手中托着一束青铜制作的竹简。怪矣哉!这是黄帝?再搭凉棚仔细打量,粗长的青铜竹简赫然闪光,简面三个大红字隐隐可见——商君书!
吕不韦一时愕然。这殿前大池的石山上矗立的指南车,原本一辆人人皆知的黄帝指南车。车上铜人,自然是大战蚩尤剑指南天的黄帝。这是秦惠王第一次与六国合纵联军决战前,特意铸造安放的,当年还进行了隆重的典礼。秦以耕战立国,尊奉黄帝战阵指南车,以示不亡歧路、决战决胜之壮心,再平常不过。百余年下来,黄帝指南车也成了秦王宫前特有的壮丽景观。陡然之间,黄帝变成了商鞅,青铜长剑变成了竹简《商君书》,如何不令人错愕?
“小子,又是一策。”吕不韦淡淡一笑,径自进了大殿。
秋藏朝会伊始,嬴政先向大臣们知会相关事项道:“诸位,得十三位老臣上书,请改黄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,以昭商君法治为治秦指南之大义。本王思之再三,商君之法经百余年考验,乃成强国富民经典,须臾不可偏离。是以,准在王城改铸黄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,并特准咸阳南门立商君石刻,筑法圣苑。两事之意,无非昭明天下:商君法治,乃大秦国万世不易之治国大道。诸位若有他意,尽可论争磋商。”
殿中一时默然,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齐聚向了吕不韦。
秦王的申明说辞,令吕不韦大出所料。常情忖度,年轻的秦王与他年轻的谋士们目下只能与他暗中斗法,不会将此事公然申明于国。理由只有一个:假若年轻的秦王果真维护商君法治,公然论战则于秦王不利。亘古至今,大国一旦确立了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,绝不会轻易挑起治国主张之争端,以免歧义多生人心混乱。目下情势,《吕氏春秋》尽管已经引起朝野瞩目天下轰动,但要被秦国接受为治国经典,尚有很远距离。唯其如此,吕不韦一门期望公开,期望论战,以收说服朝野之功效。年轻秦王的护法派,则必然要遏制《吕氏春秋》流播,遏制公开论战。否则,咸阳令蒙恬为何要逼迫吕不韦撤除《吕氏春秋》?
今日,年轻的秦王公然将此事申明于朝会,并许“尽可论争磋商”,何意也?尚无定见?不对。方才秦王说辞显然一力护法。是护法派没想明白此举对自己不利?也不对。纵然秦王想不到,李斯、蒙恬、王绾这几个才智之士都想不到吗?吕不韦一时揣摩不透其中奥秘,但却明白目下局势:此刻自己若不说话,非但失去了大好时机,反而意味着承认《吕氏春秋》与秦国格格不入,轰动天下的张挂悬赏,便会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。
当此之时,无论如何都得先昌明主张。
“老臣有言。”吕不韦从首座站起,一拱手肃然开口,“秦王护法,无可非议。然,孝公商君治秦,其根本之点在于应时变法,不在固守成法。老臣以为,商君治国之论,可一言以蔽之:求变图存。说到底,应时而变,图存之大道也。若视商君之法不可变,岂非以商君之法攻商君之道,自相矛盾乎?唯其求变图存,老臣做《吕氏春秋》也。老臣本意,正在补秦法之不足,纠秦法之缺失,使秦国法统成万世之范。据实而论:百余年来,商君法制之缺失日渐显露,其根本弊端在刑治峻刻,不容德政。当此之时,若能缓刑、宽政,多行义兵,秦国大幸也!”
“文信侯差矣!秦法失德吗?”老廷尉昂昂顶来一句。
吕不韦从容道:“法不容德,法之过也;德不兼法,德之失也。德法并举,宽政缓刑,治国至道也。法之德何在?在亲民,在护民。今秦法事功至上,究罪太严。民有小过,动辄黥面劓鼻,赭衣苦役,严酷之余,尤见羞辱。譬如,‘弃灰于道者,黥’,便有失法德。老臣以为,庶民纵然弃灰,罚城旦三日足矣,为何定要烙印毁面?山东六国尝云:秦人不觉无鼻之丑。老夫闻之,慨然伤怀。诸位闻之,宁不动容乎!《易》云:坤厚载物。目下秦法,失之过严,可成一时之功,不能成万世之道。唯修宽法,唯立王道法治,方可成大秦久远伟业。”
“文信侯大谬也!”老廷尉又昂昂顶上,“秦法虽严,然却不失大德。首要之点,王侯与庶民同法,国无法外之法。唯上下一体同法,根本不存厚民、薄民、不亲民之实。若秦法独残庶民,自然失德。惜乎非也!便说肉刑,秦人劓鼻黥面者,王公贵胄居多,庶民极少。是故,百姓虽有无鼻之人,却人无怨尤,敬畏律法。再说弃灰于道者黥,自此法颁行以来,果真因弃灰而受黥刑者,万中无一!文信侯请查廷尉府案卷,秦法行之百年,劓鼻黥面者统共一千三百零三人;因弃灰而黥面者,不过三十六人。果然以文信侯之论,改为城旦三日,安知秦国之官道长街不会污秽飞扬?”
“老臣附议廷尉之说!”国正监霍然站起,“文信侯所言之王道宽法,山东六国倒是在在施行。结局如何?贿赂公行,执法徇情,贵胄逃法,王侯私刑,民不敢入公堂诉讼,官不敢进侯门行法。如此王道宽法,只能使贵胄独拥法外特权,民众饱受律法盘剥。唯其如此,今日山东六国民众汹汹,上下如同水火。如此王道宽法,敢问法德何在?反观秦法,重刑而一体同法,举国肃然,民众拥戴,宁非法治之大德乎!”
“两公之论,言不及义也。”吕不韦淡淡一笑,“老夫来自山东,岂不知山东法治实情?老夫所言王道法治,唯对秦国法治而言,非对山东六国法治而言。秦法整肃严明,唯有重刑缺失。若以王道厚德统合,方能大见长远功效。若以山东六国之法为圭臬,老夫何须在此饶舌矣!”
“即便对秦,亦然不通!”老廷尉又昂昂顶上,“商君变法,反数千年王道而行之,自成治国范式。若以秦法所反之王道统合秦法,实则侵蚀秦法根基,重回周礼御法之老路。其时也,必使秦法消于无形!”
“除了秦法,对于秦国更有不通者!”最年轻的大臣出列了。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,“在下兼领咸阳将军,便说兵事。《吕氏春秋》主张大兴义兵,以义兵为天下良药,以‘诛暴君、振苦民’为用兵宗旨。这等义兵之说,所指究竟何物?几千年没人说得清楚。惩罚暴政而不灭其国,是义兵,譬如齐桓公。吊民伐罪而灭其国,也是义兵,譬如商汤周武。《吕氏春秋》究竟以何者为正道?不明白!果真如义兵之说,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?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,听任王道乱法,残虐山东庶民?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,终归不灭一国?若是大秦兴兵统一华夏,莫非便不是义兵了?”
“对!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!”
老将军桓龁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,使大臣们忍俊不禁,死劲憋住笑意,个个满脸通红,喀喀喀一片咳嗽喷嚏之声。
吕不韦正襟危坐,丝毫没有笑意,待殿中安静才缓慢沉稳道:“义兵之说,兵之大道也,与兴兵图谋原是两事。大如汤武革命,义兵也。小如老夫灭周化周,义兵也。故,义兵之说,无涉用兵图谋之大小,唯涉用兵宗旨也。目下秦国,论富论强,皆不足以侈谈统一华夏。少将军高远之论,老夫以为不着边际,亦不足与之认真计较。若得老成谋国,唯以王道法治行之于秦,使秦大富大强,而后万事可论。否则,皇皇之志,赳赳之言,徒然痴人说梦矣。”
殿中肃然无声,急促的喘息声清晰可闻。吕不韦话语虽缓,然却饱含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讥刺与训诫。这讥讽,这训诫,明对蒙恬,实则是对着年轻的秦王说话——稚嫩初政便高言阔论统一华夏,实在是荒唐大梦。秦王年轻刚烈且雄心勃勃,若是不能承受,岂非一场暴风雨便在眼前?大臣们一时如芒刺在背,举殿一片惶惶不安。
“本王以为,丞相没有说错。”
高高王座上一句平稳扎实的话语,殿中大臣们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一王族老臣突然冷笑:“文信侯之心,莫非要取商君而代之?”
“此诛心之论也!”吕不韦霍然离开首相座案,走到中央甬道,直面发难老臣,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哀渗透在沙哑的声音之中,“老夫以为:无人图谋取代商君,更无人图谋废除商君之法。吕不韦所主张者,唯使大秦治道更合民心,更利长远大计。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”吕不韦说罢,独立甬道而不入座,钉在王阶下一般,大殿气氛顿时一片肃杀。眼看一班王族老臣还要气昂昂争辩,王座上的嬴政淡淡一挥手:“文信侯之心,诸位老臣之意,业已个个陈明。其余未尽处,容当后议。目下之要,议事为上。”
于是,搁置论争,开始议事。
吕不韦又是没有想到,几个经济大臣没有做例行的府库归总。也就是说,秋藏决算根本就没有涉及。朝会所议之事,也没有一件丞相不能独自决断的大事。片刻思忖,吕不韦再度恍然,秦王政的这次朝会,其实只有一个目标——要他在朝堂公然申明《吕氏春秋》所隐含的实际政略,再度探察他究竟有无“同心”余地。王绾一说,李斯二说,咸阳都尉三说,蒙恬四做,今日第五次,是最后一次吗?
“小子好顽韧,又是一策也。”
至此,吕不韦完全明白:嬴政已经决意秉持商君法治,决意舍弃《吕氏春秋》。同时,却仍在勉力争取他这个曾经是仲父的丞相同心理政。然则,自今日朝会始,一切都将成为往昔。双方都探知了对方根基所在,同心已经不能,事情也就要见真章了。吕不韦有了一种隐隐预感,真章不会远,很快就要来临了。
九月中,秦王特急王书颁行:立冬时节,行大朝会。
这时的秦国,外无大战,内无动荡,是唯一能从容举行大朝会的国家。举凡大朝会,郡守县令边军大将等,得一体还国与会。这是年轻的秦王亲政以来第一次以秦王大印颁行王书,没有了以往太后、仲父、假父的三大印,自然意味深远。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,无不分外敬事,接书之日,安置好诸般政事军事,纷纷兼程赶赴咸阳。期限前三五日,远臣边将业已陆续抵达咸阳,三座国宾驿馆眼看着一天天热闹起来。新朝初会,官员们先期三五日抵达,一则是敬事王命,再则也有事先探访上司从而明白朝局变化之意。
秦国法度森严,朝臣素无私相结交之风,贵胄大臣也没有大举收纳门客的传统。然则,自吕不韦领政十余年,诸般涉及琐细行止的律条,都因不太认真追究而大大淡化。秦国朝臣官吏间,也渐渐生出了敬上互拜、礼数斡旋的风习,虽远不如山东六国那般殷殷成例,也是官场不再忌讳的相互酬酢了。尤其吕不韦大建学宫大举接纳门客之后,秦国朝野的整肃气象,渐渐淡化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松动开阔风习。此次新王大朝非比寻常,远臣边将们都带来了“些许敬意”,纷纷拜访上司大员,再邀上司大员一同拜访文信侯吕不韦,自然而然地成了风靡咸阳的官场通则。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